研討會 / 工作坊
透過研討會、工作坊,發展研究、自我培力、跨界交流。
單親媽媽勒斃雙子案,判決之後— 司法、性別、社福政策觀點座談會側記(上)
文/吳奕靜(廢死聯盟執行秘書)
編按:
一年多前,吳姓單親媽媽勒斃子女案遭一審法官判處死刑,引起許多報導和評論;今年3月,案件隨著最高法院判決以無期徒刑定讞而告一段落。過去廢死聯盟也曾接觸鄭文通案、李宏基案,類似案件總是一再提醒著,我們身處的社會裡,要在經濟的負擔、育兒的壓力、家庭的照料之間取得平衡,是多麼困難的事情。「單親媽媽勒斃雙子案,判決之後」座談會,邀集承辦案件的律師團、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分別從司法、性別、社福政策等觀點,盤點本案突顯的問題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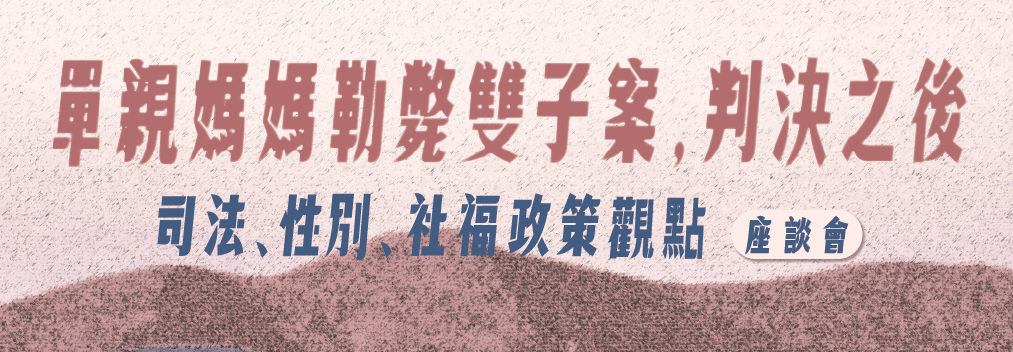
單親媽媽勒斃雙子案......
林鴻文律師簡介本案,吳若妤在1990年出生,有一位大一歲的哥哥。因為生父有家暴的行為,母親帶著她與前夫所生的兩位姊姊一起生活。基於這樣的生長背景,吳若妤對「家庭」有著更多的嚮往。有了交往對象後,過去曾多次墮胎,擔心身體不堪承受的她這次選擇生下孩子,並跟孩子的父親結婚。然而一雙兒女接連出生後,吳若妤與丈夫雖辦理結婚,實際上卻沒有生活在一起。在育兒的分工上,兩個孩子主要由吳若妤扶養照顧,和孩子的父親正式離婚時,吳若妤僅二十初歲,必須一手擔起房租、兩個孩子的學費和生活起居,家中沒有人能夠提供經濟或托育支援。
本案律師團曾訪談吳若妤的朋友、孩子的學校老師,大多認為兩個孩子與吳若妤感情深厚。老師甚至一再強調,雖然家境不好,但做母親的總是很照顧孩子、盡量滿足孩子的需求,所有學校活動她幾乎都親自出席。在案件發生前,吳若妤因為找不到工作而憂鬱症復發,即使持續就診,仍需要安眠藥及鎮定劑來協助睡眠。當她向前夫或家人表達有輕生的念頭時,卻被當作是想要擺脫責任,這一切將性格好強的她逐漸推向懸崖。當時她帶著孩子與兄嫂一家共七口一起住在一戶二室的空間,常跟兄嫂因為生活習慣與教養孩子的方式產生摩擦,她曾改向姐姐求救,但緩不濟急。在無工作、無存款的情況下,吳若妤開始解除保單試圖調度經濟,狀況卻沒有好轉,連體重也下滑到過瘦。她曾嘗試自殺,在自殺前還多次詢問哥哥,孩子能否託付給哥哥照顧,但遭到拒絕。
最後即使學校老師查覺吳若妤有輕生念頭並通報社會局,仍來不及挽回這場悲劇。重新探討吳案並不是要再次非難吳若妤的犯罪,而是她的確做了錯事,但我們能否透過這個案件,回到孩子照顧者的處境,想一想案件發生的原因,避免更多的憾事發生。

法院與單親媽媽的距離:判決分析
廖蕙芳律師分析,由於本案犯罪事實沒有爭議,法院如何量刑便會成為關鍵的因素。以律師團的辯護方向而言,會以三個方向為重點,其中第一個是有無刑法第19條中所規範精神障礙的問題,其次是刑法第59條中關於「情堪憫恕」的狀況,最後則是刑法第57條中衡量被告一切情狀的部份。由法院各審的判決也可看到都是從這幾點來判斷。
律師團認為,吳若妤案在地方法院的判決架構就已經被定調,到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都是延續著一開始的判決架構。當時地院的精神鑑定認為吳若妤犯案時的精神狀況「略有缺損」,法院認定並不影響其犯罪行為。而關於量刑的部份,則分別以「被告經濟狀況不佳...不思尋求協助...」、「被告僅因一時不順遂…實不宜輕縱之...」認為被告吳若妤是因為「一時的不順遂」才會選擇殺子。這樣的標準不但是不顧吳若妤當時個人及自身的情形而下判決,甚至以吳若妤當時的困境,作為「不能輕縱」的加重量刑的理由。對吳若妤而言,實在不公平。由此也透露出法官對於吳若妤處境的不理解。
高等法院判決無期徒刑的理由,同樣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加重吳若妤的刑責,也無精神障礙的適用,甚至關於量刑的部分,判決書上寫著「被告僅因經濟壓力,即對子女下重手,手段兇殘。且被告不思有同住家人可以尋求協助,反執意殺害子女,也沒有刑法59條資堪憫恕之適用」宛如道德審判,以法官或一般生活無虞的人為標準來理解吳若妤的犯罪,甚至將被告的困境視為重判她的理由。另外引用兒童權利公約稱吳若妤之犯行不宜寬待等,來加重被告的罪刑,其實是對公約的錯誤理解與運用。而最高法院加深高等法院的論述後就駁回上訴,最終本案無期徒刑定讞。
廖律師指出,這是對吳若妤很不公平的判決,在這個殺子後自殺的案件中,三審法院判決皆無提及被告試圖自殺的事實,也未曾考慮精神鑑定中吳若妤的智能落在邊緣程度,是否影響她的思考模式。在量刑的過程,沒有回到被告身處的困難來審酌,反而指責其作為母親的「失職」與殺人罪刑。這也讓人反思,國家的社福制度有沒有更多施力的空間,承接在工作與育兒中兩難的照顧者?

一個始終在尋找歸屬感的人:訴訟背後
李晏榕律師分享,經歷三級三審,可以發現法官跟律師團對於吳若妤案的理解很不同,社會大眾的觀點也很兩極。法院和部分觀點可能是「無論生活再怎麼艱辛,都不應該殺掉自己的孩子。」因為對多數人來說,這是難以想像的事情。尤其吳若妤案中,受害的兩個孩子相較於其他可見於新聞的案件而言,他們健康活潑而非面臨身心疾病,需要更多的輔助。而律師團與另方面的意見則是,作為母親是有多麼絕望才會選擇奪走孩子的生命。
吳若妤案在一審時遭判死刑,引起大眾的討論,案件上訴到高等法院時,李律師發現,法院與檢察官對於精神鑑定、量刑調查等都一致同意,但當律師團表達希望可以再做更詳細的補充調查,法院卻不同意。這樣的狀況也讓律師困惑,是不是當法院決定審判不朝向判死刑的方向進行,就可以免去進一步的調查。
而在準備量刑前社會調查時,律師團訪問了吳若妤與身邊的重要他人,讓李律師印象深刻的是,其實有時候作為一個人,真正的心情與痛苦,不見得是身邊最親近的人才能夠感同身受的。當時曾訪談吳若妤同為單親媽媽的朋友,她就表達,即使大家習慣「單親媽媽」這種身分、族群的存在,但距離理解單親媽媽在生活上面臨的困境、需要什麼協助,卻還是很遙遠。許多女性在決定生子又面臨情感關係結束時,就連要回到原生家庭求助,都有可能受到父母或親戚的責難或異樣眼光。因此反而是在這段最需要支持的日子中,這些單親媽媽不會選擇一離婚、分手就帶孩子回娘家生活,而她們在失去重要關係的情況下,仍必須負起養育與經濟重擔。那位朋友向李律師表示,自己也曾經想要帶著孩子走(離開人世),因為整個社會認為這都是「自己的選擇」、「為什麼撐不下過去」,對一般人來說也許稀鬆平常的評價,卻可能擊倒苦撐已久的單親媽媽。
吳若妤也曾跟李律師表示,單親媽媽很難找到工作,她曾經做過各式各樣的工作,甚至騎機車沿街找尋徵人啟事。但以她的學經歷,通常能找的工作會是低薪、高工時、且假日需輪班的服務業,她曾經找到業務助理,但每隔周六就要上班,她的家人沒有辦法協助托育、教養方式也與她所認同的不符,最後她詢問評估假日托育高昂的費用後,還是放棄了這份工作。遺憾的是,這些社會環境的問題沒有機會呈現給法官,讓法官更認識吳若妤的處境、理解她在經濟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已經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李律師眼中的吳若妤,是位一生都在追求屬於自己歸屬感跟家庭的人。
此外,當時鑑定團隊對吳若妤與其重要他人的訪談,因為受到疫情影響,當時都是通過電話,而非親自面訪。律師也曾要求鑑定團隊到法院進行交互詰問,但法院並未允許,這都是判決書無法呈現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