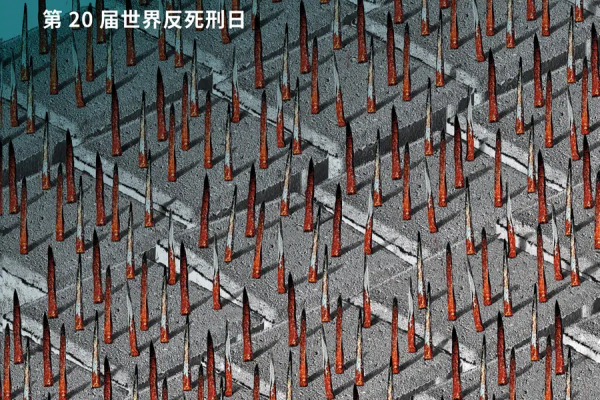電子報
廢死聯盟說的話,是為《廢話》。
在2010年的死刑爭議裡,我們受封為「最邪惡的人權團體」,我們的主張,看起來確實狗吠火車,所以《廢話》也就是「吠話」。知其不可而吠之,汪汪!《廢話電子報》於2012年2月首次發刊,每個月發行的廢話電子報是廢死聯盟實踐與社會溝通的方式之一,我們期許自己用淺白、易懂的文字,透過定期的發刊,持續跟社會對話。
沒有一無可取的人—薛煒育律師專訪
文/羅禮涵(廢死聯盟倡議專員)
「當律師可以陪伴受扶助人,可以更有深度去了解這個人,這是法官和檢察官不可能做到的。也是我一直都沒有後悔當律師的原因。」
今年是薛煒育律師在法律扶助基金會(以下簡稱法扶)擔任重刑組的專職律師邁入第六年,在此之前,他曾擔任過民事庭的法官助理,也在主打民事案件的事務所擔任受雇律師。「當時的薪水不錯,甚至是用年薪計算的。但到了要續簽的時候,我突然覺得這樣意義何在?」因緣際會,法扶開出專職律師的職缺,煒育就這樣進入了法扶。

第一個死刑案件上門
還在前事務所擔任受雇律師時,接了第一件法扶的案件,讓煒育至今仍印象深刻。案件內容涉及殺人,有遭判死刑的風險,被告是一個計程車司機,社經地位稱不上好。當時煒育陪著他一到三審,最後無期徒刑定讞。會接這個案件,只因為初生之犢不畏虎,身為律師,什麼案件都要試試看。這位被告的前妻和扶養他長大的阿姨,一直非常關心被告的狀況,讓煒育看見人性溫暖的那一面。被告的兩位家人起初並不願意出庭成為聚光燈下的焦點,但透過煒育一次次解說訴訟程序、案件進度,到二審時煒育成功說服兩位出庭作量刑證人,說明在他們眼中的被告是個怎麼樣的人,至少讓法官知道這個人並不是只有案件中的面向。他還是阿姨心目中可愛的晚輩、前妻和未成年子女心目中的好伴侶、好爸爸。此案讓煒育深深體悟,一個社會案件終究是屬於人的問題。「我是不是可以多幫一下這些人?」這個放在心裡深層的叩問,悄然地埋下日後煒育選擇成為法扶專職律師的種子。
與當事人互動需要耐心,但是值得開心
來到法扶才兩個月,就接到王景玉案的起訴書。一週後,又接到一件思覺失調患者在捷運上殺警未遂的案件。煒育苦笑說自己不但是重刑,還是精神專股。當時這些案件跟著前輩律師組團一起進行,也很快地讓他學習到系統性的辯護策略和方向,包含刑法19條、57條、國際公約、教化可能性鑑定、量刑前社會調查等等,為煒育後來碰到的其他案件奠基了著力點。
從專辦民事和商務案件的事務所來到法扶,還是有許多辛苦的磨合。除了原以為專職律師可以準時上下班外,最大的感受是在法扶碰到的當事人,溝通成本通常會比較高。「過去我的工作就是看契約、談判。你不用跟我講那麼多,告訴我底價多少就好,我回去報給公司,就是這樣。」但這個過程煒育總覺得好像少了點什麼,也一直很困惑這是不是他真正想要的訴訟律師角色。
「現在跟法扶的當事人互動常常需要很多耐心,但我是開心的。」
煒育說,他曾遇過一個當事人,今天才說把我當最好的朋友,電話簿裡面只有我和他媽媽的電話,第二天就對我說律師你怎麼不去死一死。遇到這種情況當然會很洩氣,但煒育也試著換個角度思考,生病導致與人應對極端反覆的狀況,恐怕不會是當事人自願的。而他的工作正是要協助這樣的當事人跟法院對話,到底怎麼樣的判決結果,對個案、對他的家人、對被害者家屬、對社會,都可以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煒育最後用「不挑食」做為比喻,說他自己不會挑案件。「這種案子很多律師不接,或是很快就解除委任,但這個案件不重要嗎?它很重要啊。它就是台灣社會上的問題,如果沒有律師要做,對被告、對社會都是不正確的。既然需要有人做,那就做啊!可能我少根筋吧,就一直接到現在了。」
被當事人拉住才能走到現在
問及這幾年來最大的成就感跟挫折感分別是什麼。煒育立刻自嘲:「我沒有成就感啊!」一起重大刑案發生,就表示社會上有人遭遇困難,而每一個案件他都還是會找到自己做得不足的地方、還可以有更好的地方,或多或少會留下遺憾,成為未來辦案的養分。
挫折感很多:書狀寫不出來、被當事人委任後又遭退貨、被法官臭罵一頓,這些是家常便飯。煒育分享,他人生中最大的挫折是,有案件在自己的手中死刑定讞。
「宣判那天我不敢面對,我沒有把握、很害怕。我的學習律師聽判完跟我說結果,我跟他說我知道了,你回來吧。」這個案件在律師團看來,與法院認定的犯罪事實有所落差。此外,從當事人的家庭背景、智識程度、個性等等,律師團也都認為沒有判死的必要。「選任辯護人掛我的名字,主文是死刑,這是我第一次為了一個案件掉眼淚。」煒育說。當時那件死刑案件重挫煒育好一陣子,讓他陷入一段自我懷疑、不想接案的低潮期。「但很神奇的,就會突然間被過往的當事人拉住。」他自認運氣滿好的,每當倦怠時,以前的當事人或家屬都會「適時地」跑出來找他一下。可能是問案件進度、諮詢法律問題,但這都讓他覺得自己被需要、被信賴,也給他更多的信心,好像自己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爛,就跌跌撞撞走到現在了。
「我曾遇過一個訴訟結束都過了八、九年的當事人,每年還是會去廟裡幫我點光明燈;也遇過一個當事人幾乎全家大小的法律問題都會向我請教,我都笑稱這就像是家庭醫師的概念,我是他們的家庭律師了吧。」 對煒育而言,這些人對他的信任和需要,是他可以繼續堅持下去的理由。
「可能到有一天大家都不信任我、不需要我了,那我就去送Food Panda吧!」煒育笑著說。
「我比小孩更吵!」—跟家人在一起時最開心
煒育的太太沒有真正接受他的工作內容,但這絲毫不影響家人之間的愛,太太還是很鼓勵他實踐自己想做的事情,給予他很大的支持和安慰。 至於一雙可愛的兒女,因為年紀都還小,只知道爸爸的職業是律師,但對於律師這個職業並沒有太多的想像,不過煒育會嘗試分享自己在工作上遇到了怎麼樣的人。「我會跟他們說,不要覺得有些人好像跟我們不一樣,我們就對他們有不一樣的眼光。有些人可能生病了,或是可能觀念跟我們不同,但我們要尊重人家。」這樣的機會教育比起是否真的了解律師這個職業,來得更重要些。
「跟家人在一起當然是最開心的時候。」平日工作再繁忙,假日也會盡量空下來帶小朋友出去走走,這對煒育來說也是放鬆跟充電的時候。不怕小朋友吵,「我比他們更吵啊!」卸下律師身分的煒育,就像個大男孩陪小朋友玩,一起吵吵鬧鬧有什麼不好?他接著說,自己超痛恨新冠肺炎,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少了很多帶小朋友出去的機會。
「有一次在吃早餐時,我問我女兒,要不要我去學校當義工爸爸,做法治教育宣導。我女兒立刻說不要。你看,連女兒也退貨我!」煒育苦笑地跟我們說著。
談到接案對自己和家人的影響。煒育回憶起之前接王景玉案時,女兒才一歲多,看到新聞時也難免有投射和擔心,開完第一次準備程序庭後就收到臉書陌生人的的私訊「問候」。「我只是看得比較開,但不代表不會受影響。」但煒育也很快就思考調適過來,那些留言和謾罵就只是情感性的發言,新聞不會報得鉅細靡遺,也不像律師、檢察官和法官,或真正的被害者家屬透過訴訟參與,看到案件的全貌以及更多案件的細微處。
保護家人、調適心情、理解大眾的情緒,而回到工作本身,受委任是為了保障當事人在法庭上的正當法律程序,這才是要往下做的事情。

為什麼支持廢死?因為沒有人該死啊!
「我一直在想國家為什麼可以殺人,以及,一個人真的會壞到一無可取嗎?也許是我經驗有限,但我還沒看過這樣的人。」當然也會遇到不喜歡的當事人,讓煒育很想掐死對方,他會偷偷抱怨,或在心裡對當事人翻上無數個白眼。但從心理師、社工師訪談的資料中,看看當事人的父母、家人、朋友,甚至是以前教過他的師長,會發現他的人生中還是有一些比較光輝、正面的東西。
「我還沒看過一無可取到報廢也不覺得可惜的人。」
煒育說,他看到更多是不願意放棄犯罪者的人。他就曾遇過連爸媽都放棄,不願意出來作證的情形,但最後他的國中舞蹈班老師卻願意出來作證。他們只有一年的師生的緣分,老師還是願意出來告訴法院這個被告有好的地方。
所以真的有人非死不可嗎?不能有其他替代措施嗎?這是煒育一直在想的。
國民法官制度、憲法訴訟—回歸源頭,好的溝通和對話才是解方
關於明年即將要上路的國民法官制度,煒育幽默也帶點無奈地笑說,「你們不應該問我會不會接,要問的應該是我會不會是第一個接?」 國民法官上路對於律師的負荷量大大提高。法扶採取的應對方式是增加酬金、以團隊合作模式減輕單一律師的負擔。
至於對國民法官制度的想法,煒育認為集中審理確實會讓案件變得困難。過去可以用書狀、文獻向法院「盤點存貨」式地列出的量刑基準、教化可能性、人權公約、一般性意見等,但國民法官制度上路後顯然需要不同策略。因此,律師要如何建造好的對話基礎,口條上如何簡明扼要地談什麼是直接故意、間接故意等法律專業術語,來讓國民法官理解甚至認同,都是挑戰。此外,撇開犯罪事實,要如何跟國民法官述說當事人的故事,包含他的生命歷程、成長背景、犯罪動機等,這都是未來律師需要面對的新課題。
至於憲法訴訟,煒育說自己其實有點期待。辯論有公開直播,讓更多人可以排除時間和地域的限制,一起聽聽看。以廢死相關的憲法訴訟來說,也會期待更多台灣人可以趁機更深入地去想一想關於死刑議題的論述。社會新聞往往都是很片面的資訊,比如:誰誰誰又逃死、廢死就是不知人間疾苦、死刑犯監獄蓋在你家旁邊啊…這些資訊其實無助於討論,我們可以回到實務層面,以它的正當性跟必要性去討論。
後記
訪談結束後,我們問煒育,他可以立刻退休以及台灣立刻廢死,如果只能選一個,要怎麼選?他雖然無奈但還是很快地給出了答案:「好啦,台灣立刻廢死啦!」
以為會是艱難的二選一,煒育卻不假思索。他說,總是要給一點正能量。
感謝煒育用他繼續厭世的辦案,換台灣盡早的廢死。雖然是玩笑話,但希望我們真的可以做到。廢除死刑,像是煒育說的,因為沒有一無可取到報廢也不覺得可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