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報
廢死聯盟說的話,是為《廢話》。
在2010年的死刑爭議裡,我們受封為「最邪惡的人權團體」,我們的主張,看起來確實狗吠火車,所以《廢話》也就是「吠話」。知其不可而吠之,汪汪!《廢話電子報》於2012年2月首次發刊,每個月發行的廢話電子報是廢死聯盟實踐與社會溝通的方式之一,我們期許自己用淺白、易懂的文字,透過定期的發刊,持續跟社會對話。
我們都是翻譯者—《審判王信福》導演張娟芬、錢翔對談
文/吳奕靜(廢死聯盟執行秘書)
「我才跟劇組的美術設計人員說,我有一種闖禍的感覺。」娟芬說。
「這就是一個轉譯的過程。」錢翔表示。
《審判王信福》僅用三天時間拍攝完畢,且多數演員皆為素人,而劇組團隊事前對於冤案、冤案平反者演員們認識並不多,也因此激盪出不少火花。從兩位導演的視角來看,《審判王信福》又是一部什麼樣的電影?

劇本先行
《審判王信福》是一部劇本先行的電影。錢翔說明,有許多橋段與設計都是在劇本階段就已經大致抵定,因此整體來說可以這麼比喻,身兼編劇與導演的娟芬是「腦」,而劇組團隊就是「手」。對娟芬而言,《審判王信福》整個劇場如何將文字、理念的人事物實踐在片場中十分具有魔力,她曾和劇組的美術人員說,自己有種闖禍的感覺。因為寫下了什麼,都變成具體的影像呈現,不僅只是細節,還要符合時代脈絡。兩人談到劇中的法庭場景,其實就充滿空間的政治學。三位法官是坐在檯上的,遠離律師、被告以及檢察官,而高度又要架幾公分才合適?這些問題都會影響觀眾對於階級、權力關係的感知。一旦涉及影像,那早已不僅只是冤案事實陳述也不再只關乎電影美感。
兩個世界
正因為是兩個不同領域的合作,即便是作為「手」的團隊,也會在上述的準備、考究道具以及拍攝期間學到一些法律相關的知識、甚至對冤獄有所認識。「那是有趣的,平常可能不太會碰觸到這樣較深的司法相關議題,它本身就是收穫,不然可能一輩子跟這些事情牽不上關係。」錢翔說道。他認為「我們都是翻譯者」,娟芬將法院的卷宗、判決翻譯成使人更容易理解的文字,而自己和劇組團隊負責把娟芬的文字翻譯成為影像,這是一個轉譯的過程。過程中每個人會從原初的東西得到一些什麼,那些在原本領域中自己所不知道的,都會產生化學作用。
演員的表現是讓娟芬最驚喜的,原先劇本機械式的問答,經由演員們的設想,帶了新的詮釋到劇本中,為這個劇本添加了一些藝術的元素,使劇本更加鮮活。尤其飾演檢察官的馬世芳,舉重若輕地就演出檢察官的不耐、倦怠。片場中但凡只要坐上那個檢察官的位置,他就是一位檢察官,大家走來走去他也不理。即使是素人,幾乎每一位演員都做足了功課。「顧玉玲的演技也非常出色,素人演員有意思的地方就在於,她演一個跟她平常很不一樣的角色,平常可能是到哪裡都很有自信也自在的人,去飾演一個相對緊張的、擔憂的角色。有些很細節的處理很讓人驚豔,比如劇中有一個畫面是張清梅作為證人出庭時,王信福的反應。飾演王信福的徐自強看著證人席,演出那個不肉麻但柔情似水的眼神。」娟芬說。
錢翔:拍電影像玩碟仙,也像炒菜

談到電影製作過程,錢翔謙虛地表示從來不覺得是導演要做什麼,「很像是玩碟仙,三、四個人手放那個碟子上,指出各自預測的方向或能量的角力,但它就會往沒有人指的方向走,它會自己往那個方向走去。」不同於其他創作,寫作可能是文字與作者之間,但影像是一種集體創作,個人創作的部分相對容易被刷淡。而電影本身在這些角力下會有機性地產生一些自身的東西。
《審判王信福》充滿倡議的意圖,邀請觀眾迫近司法的真實現況。而原初便是在當時在任的藝科中心主任王盈勛與藝科中心的同仁、顧玉玲以及兩位導演的討論中誕生,包含法官的角色要找三位冤案平反者也是事先就確定。拍攝前又經過三到四次劇組團隊與錢翔開會進行分鏡的設計,也是因為這樣的過程以及素人演員們的無償貢獻才得以完成。
錢翔也說:「拍電影像炒菜,假如中間有哪項因素換了,可能就不會是原來的樣貌。」因此,如何以現有的材料組成期待的東西才是比較重要的。娟芬也有感於跟剪接師的討論,也許原先記得某個鏡頭是好的,但最後以呈現的結果來看,剪接師的選擇總是更適切。
治癒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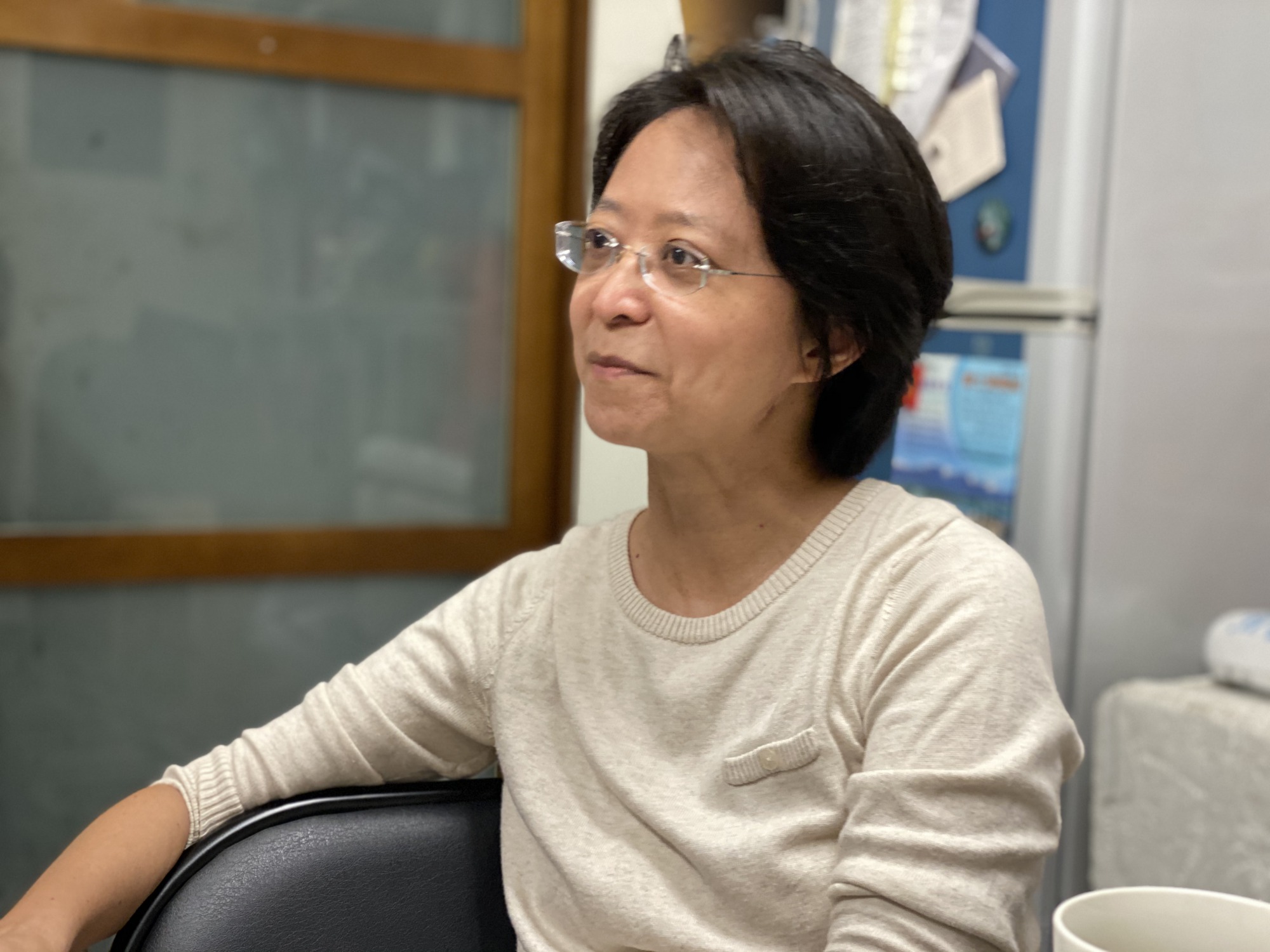
娟芬則說:「經歷整個拍攝,很震撼當一個東西變成影像時,它的威力會遠遠超過我們原來所設想的。鄭性澤也說,他坐在法官席上,會不斷想起以前的事情。」除了為戲安排的心理戲,素人演員們心中也有更多感觸持續發酵著。錢翔補充黃致豪律師在片場曾提及的,但也許戲劇會帶來某些治癒的力量。事實上與真實人生互相呼應的劇本也經常在其他電影中上演,這也是《審判王信福》的巧思,對於認識冤案的人可說是彩蛋無窮,而對於不認識冤案的人,也能夠快速地認知、感受到法庭的模樣與節奏。
正義有沒有更溫柔的方式?
也許我們在尋找的主要是:正義有沒有更溫柔的方式?談及死刑,娟芬多年前經歷思辨,寫下《殺戮的艱難》,至今也依然參與在司法領域的倡議中。錢翔陷入深思,拉長了的歷史時間、空間,他認為國家的心態也許一直更傾向於擁有權力時,就遵循經濟學法則便宜行事,例如死刑,就像拍死一隻蚊子也不會產生憐憫之心那樣。而當我們試圖將權力拉往人民自身、拉往人權的價值觀時,往往我們在對抗的還是古老的那個世紀,固守舊有的價值觀如同幽靈,揮之不去。而可以確定的只有,我們不會選擇忽略那些「活在古老世紀的人們」。錢翔的自我定位則比較像是旁觀者或者閱讀者。
僅差幾歲的兩位導演,在讀書年代正好碰上台灣社會運動蓬勃發展時期,娟芬選擇深研議題,以寫作參與不同議題的社會運動至今;而錢翔當時作為學生、工作人員,揹著錄音機、攝影機就跟著井迎瑞、李泳泉、吳乙峰這些現在的大師們出去四處拍。對他而言,當時的景況是前所未見的,這些訓練也並非事先啟蒙思想,而是時代來了,便接收了,後來才漸漸去思考國家、主權、意識形態等問題。

《審判王信福》的前身其實是模擬法庭,救援中的其他冤案也許可以期待找到新證據做科學鑑定,但王信福案沒辦法。此案所用證據多為證人口述,然這些供述證據卻前後不一,甚至兩位關鍵證人中,一位已經遭國家執行槍決,另一位則隱匿蹤跡,難以追查;凶槍上亦無驗出指紋,於是才選擇以影像呈現。也許是劇本特性使然,《審判王信福》不以吼叫的姿態傳達訊息,反而凸顯其荒謬性,力道也自然產生。即使作為一部法庭戲,《審判王信福》未必完美,但在各種條件下,《審判王信福》走出它自己的路,也期待大家能夠共同關注王信福案,共同牽出王信福的回家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