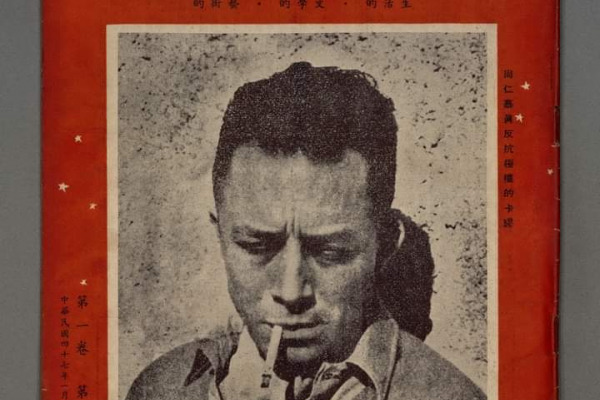電子報
廢死聯盟說的話,是為《廢話》。
在2010年的死刑爭議裡,我們受封為「最邪惡的人權團體」,我們的主張,看起來確實狗吠火車,所以《廢話》也就是「吠話」。知其不可而吠之,汪汪!《廢話電子報》於2012年2月首次發刊,每個月發行的廢話電子報是廢死聯盟實踐與社會溝通的方式之一,我們期許自己用淺白、易懂的文字,透過定期的發刊,持續跟社會對話。
斷頭台下思索卡繆:錢建榮、吳坤墉對談
文/詹斯閔(廢話電子報特約記者)
刺眼艷熱的陽光、沙灘、海洋與死刑,幾乎是卡繆作品恆常出現的元素。1913年卡繆生於北非阿爾及利亞,1960年和出版社編輯駕車回巴黎路上意外車禍死去。今日時空遠遠相隔來看,卡繆依舊迷人萬分。他激盪過無數人心,其中萬分之二是無境文化總策劃吳坤墉和高院法官錢建榮。2012年無境譯介《思索斷頭台》這本論死刑的著作,吳錢兩位在新書座談會上相知相談。時隔八年,再次邀請他們談談卡繆。

第一人:成長背景
事情是怎麼開始的?聊他們與廢死議題第一次接觸,從青春的當初說起。吳坤墉在巴黎讀社會學和政治哲學:六八學運、催淚彈、學生團體在波特萊爾走過的街巷和警察打游擊,他感受過那樣的餘溫。起初以為吳坤墉的叛逆不羈應該渾然自成。他坦言:「我以前也覺得作奸犯科的人去死,剛好而已。」一旁錢建榮附和:「我大學的時候也是。」或許自我覺醒不可能輕鬆順遂而得。

1987年台灣解嚴,當時錢建榮在輔大法律系讀書,吳坤墉則是準備進台大社會系的大一新鮮人,那是少年家戴著圓圓厚厚大框眼鏡、穿牛仔褲站三七步就自以為很酷的年代,「我們都成長於威權時期的台灣。」他們比對一下年份,其實威權沒有離得太遠;也可以說還沒完全離開。正因為強烈感受過,更需敏感戒慎。
要明澈卡繆的思想,一定要回頭看他的生平。吳坤墉強調,這也能解釋為何至今他還是那樣吸引人。卡繆誕生在法國殖民下的阿爾及利亞,極其貧窮的地方,爸爸一戰時為法國赴前線而死,這個遺腹子被不識字的純樸媽媽和阿嬤扶養長大。中學時代,哲學老師特地跑到家裡和卡繆的祖母力爭:這是我班上最優秀的小孩,千萬要讓他繼續讀書,別太早去做工。二戰德軍佔領期間,卡繆也冒著生命危險投入反抗軍的地下刊物《戰鬥報》(Le Combat),擔任編輯和記者。
荒謬和反抗
戰亂捏塑著人的思慮。卡繆成長於法國殖民下阿爾及利亞,對於當時不同族群遭遇之制度性的不公平對待,深感憤慨; 隨後一股「以種族主義為基底,用極權手段使國家強盛起來」的惡風吹來,不僅在德國與意大利,歐洲各地都見法西斯主義興起,令人憂心。此時卡繆大約二十九歲,接連完成小說《異鄉人》、哲學論文《薛西弗斯的神話》和劇作《卡里古拉》,這些著作都談到存在主義人的生命狀態,一般稱為他創作的荒謬期;之後《鼠疫》和《反抗者》等等則是所謂的反抗期。筆尖隨意志而走,卡繆的創作發展暗暗映射著時局。
「就書名La Peste 來說,譯成『鼠疫』比『瘟疫』恰當。」前任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理事長,吳坤墉耐心解釋:卡繆這本書1938年開始動筆,彼時希特勒已透過合法民選取得執政權,二戰蟄伏待起。後來1946年歐戰結束,隔年全書定稿出版。「他選擇用黑死病的意象來講納粹。」納粹德軍穿棕色制服,當時法國人稱他們棕色鼠疫(peste brune)。疾病就像某種體制權勢的毒,每個人隨時隨地都可能感染——現今肺炎病毒大流行,類似的非常狀態近在眼前——起初天真悄悄地交付讓渡,等到病毒肆虐風行之時,封城。所有意義和情感社交崩散。
二戰後各國忙著建立新社會,卡繆懷抱高度理想,但他對任何可能變得危險的政權極度小心。相較之下,沙特(Jean Paul Sartre)可說是無條件支持史達林的極權政權。兩人友誼分裂,只要卡繆提筆批評,沙特和他在 《現代》雜誌(Les Temps Modernes)的盟友們就會強烈回擊,卡繆幾乎無地容身。吳坤墉提醒我們從成長背景來想:「沙特就是一個中產階級,卡繆是很底層出身的。」錢建榮聽了有感而發:「難怪我不喜歡沙特。」1954年阿爾及利亞開始長達八年的流血獨立革命,卡繆沒為任何一方背書因而飽受批評,後來他在文壇相對黯淡安靜。1957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對他來說是意料之外的驚喜。
反對死刑的一貫精神
卡繆作品有多少成分是為了社會批評?錢建榮談起自己的解讀:「我一直覺得,他從頭到尾都想講死刑。」文學只是起點。《異鄉人》主角失手殺人被判死,其實應該算正當防衛,可是身為被告他一句話也不能說。《鼠疫》裡塔盧原先摯愛仰慕著檢察官父親,直到發現爸爸在法庭上如何用力致人於死,爾後塔盧一看到那本父親的鐵路指南就會因厭惡而發抖。關於廢死的呼籲,錢建榮猜想,可能當時法國社會還是不太理睬,所以卡繆決定不再用故事包裝,1957年《思索斷頭台》直接用社論正面對決。
或許這樣解讀一點也不「文學」,但不無幾分道理。吳坤墉稱讚錢建榮真的是卡繆知音:「這一路走來,卡繆完全知道國家要為惡的時候,可以有多可怕、多麼的壞。」即便國家在不為惡的時候,那個宰制人民的潛質仍然一脈相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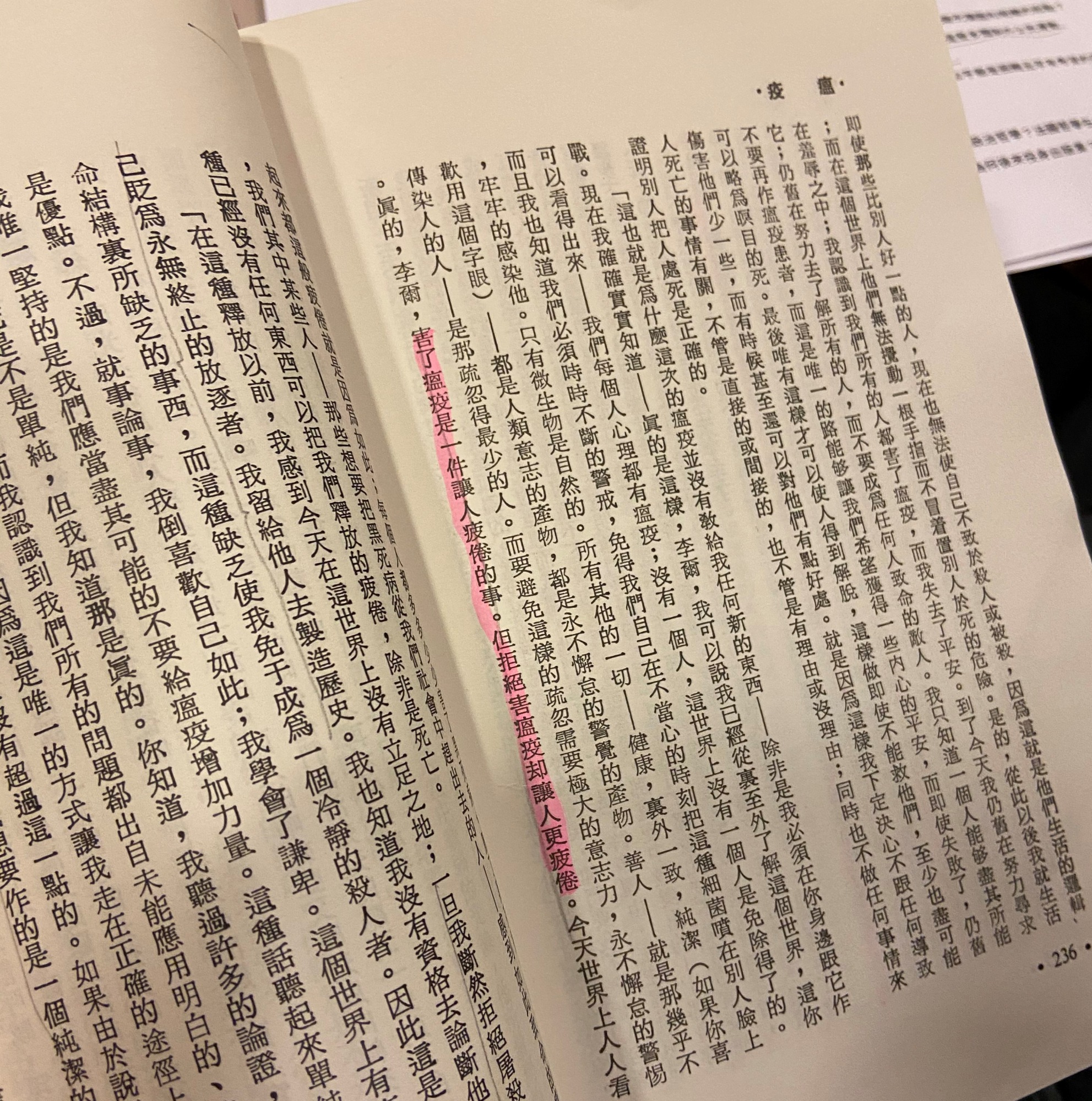
錢建榮在劃滿螢光筆的書裡翻找:「害了鼠疫是一件讓人疲倦的事,但拒絕害鼠疫卻讓人更疲倦。」身為一個拒絕信奉死刑的人,他被這句話深深打動。「其實想要殺人的慾望和氛圍就好比鼠疫。」國家可以合法殺人,這就是最大的荒謬。該如何對待荒謬?我們或許認為,法官在體制內有施展空間;錢建榮說他對個案可能有決定權,事實上多數時候他只是個被司法行政體系宰割的人。「整個城市攤掉了,你只能一個一個救。」他覺得自己像《鼠疫》裡面的李爾醫生一樣無能為力。
司法能有文學的溫度
「我常開玩笑說,我是另類司法世家。」錢建榮的父親是法警退休,母親過去經營司法院餐廳多年,家裡還送司法報紙。自小在其中沒錯,但終究帶著來自底層的眼光看整個體制,和卡繆的觀點巧相呼應。司法高權的後代往往容易站到重要位置,父執輩在黨政不分的年代做了糟糕的事,有包袱的人要怎麼推翻。或許這也是台灣司法轉型正義遲遲難推進的原因之一。
說起自己何等愛卡繆,錢建榮像一個放學後還得補習、肩負沉重書包的小孩,跑去買熱騰騰紅豆麵包大咬一口下去那樣的安慰和滿足。笑稱自己從來都不是文青,他卻不只一次在判決裡引用文學:關廠工人案的尾巴是卡繆《快樂的死》、某次行政訴訟庭拿張娟芬《殺戮的艱難》來鼓勵原告被害人。他相信判決不只是框架和官樣行文,應該要有血有肉;所以錢建榮把一個個判決當作品來寫。
出版作為一種反抗
文學不只有溫度,還有深及價值的力量。吳坤墉出版「奪朱」系列叢書取「惡紫奪朱?何不讓它萬紫千紅」之意,盼望帶來多元思辯。他憶起一段往事:2010年以前台灣曾有四年多的時間停止執行死刑,「你看當時犯罪率也沒有提高。」他以為知識界和政治圈有起碼共識,所以打算先出版雨果的浪漫主義小說《死刑犯的最後一天》,從情感面和大眾對話。無奈當局恢復執行救民調,他回頭選擇卡繆的議論作品《思索斷頭台》為先。
談起作家和作品,吳坤墉熱切誠摯,他眼裡綻著絢爛。在他背後應該是塞納河畔咖啡店漫遊者這樣的巴黎風景。吳坤墉後來選擇回台投身出版事業:「我長時間思考和閱讀的東西,我想分享和傳散出去。」即便聲音影像媒介很重要,他認為文字與書本還是比較有助於深思熟慮。

2019年無境出版《異鄉人:翻案調查》從卡繆筆下那個沒有名字的阿拉伯佬出發,顛轉視角重寫故事。吳坤墉邀請作家卡梅.答悟得(Kamel Daoud)來台,談當代阿爾及利亞和阿拉伯世界種種議題,「關於殖民和脫離殖民後的狀況,在台灣一直缺乏深刻討論。」吳坤墉織起概念的網,牽引台灣讀者認識好大好大的這個世界,裡頭有政治和社會現實反省。他再三強調:「批判的政治思考是為了揭露與對抗宰制,同時追求個人與群體的自由。」其實每件事都關乎政治,文學也是。經營出版不容易,疫情又讓一切變得更加嚴峻。受訪這天吳坤墉穿一件深色西裝外套,肩膀顯得硬挺寬厚,看起來荷負沉重。
在台灣推石上山
《思索斷頭台》卡繆直球探討死刑的荒謬與惡,出版二十五年後法國廢除死刑。這本書2012年在台灣出版,「希望二十五年後台灣也沒有死刑了。」錢建榮在當時的新書座談會上這麼說。時隔八年,吳錢兩位再度聚首,來不及問問他們覺得台灣的廢死運動是退後了或前進。
作家、記者、哲學家、劇作家、知識份子和意見領袖,卡繆同時有好多身分;吳坤墉和錢建榮各是出版家譯者、學者和法官。或許這些職業分類都不涉及本質,因為他們都清楚明白最荒謬的荒謬,每天每天,在龐大痛苦沮喪失敗和一點點希望之中存在。他們反抗,他們都不願讓人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