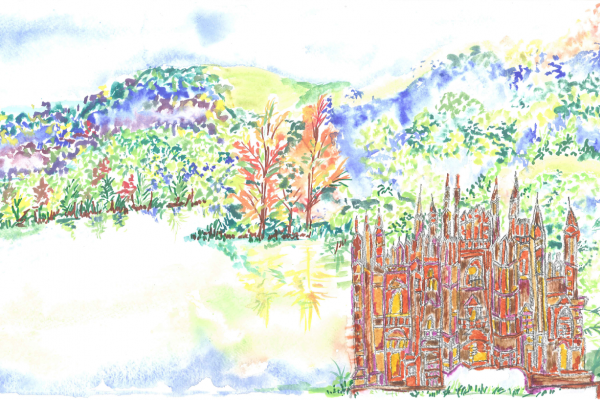電子報
廢死聯盟說的話,是為《廢話》。
在2010年的死刑爭議裡,我們受封為「最邪惡的人權團體」,我們的主張,看起來確實狗吠火車,所以《廢話》也就是「吠話」。知其不可而吠之,汪汪!《廢話電子報》於2012年2月首次發刊,每個月發行的廢話電子報是廢死聯盟實踐與社會溝通的方式之一,我們期許自己用淺白、易懂的文字,透過定期的發刊,持續跟社會對話。
冤案的洞穴與岩壁:談《審判王信福》
文/張惠菁(作家、衛城出版總編輯)
四月,顧玉玲在messenger上敲我,說了《審判王信福》的拍片計畫,問我願不願意演審判長。我立刻就答應了。其實,我心裡一直覺得,2006年我因為故宮南部分院案被起訴,官司歷時三年,這個經驗不是我自己的,可能有一天,適當的事情和時機會到來,這個經驗可以拿出來貢獻給社會。

這是一個奇怪的邏輯?按理說,可以拿出來「貢獻」的,應該要是「好事」才對。那明明不是什麼愉快的經驗,我心裡卻有那種感覺。不是諷刺,也不是帶著什麼怨恨,想說把它丟回去給誰的那種。而是真的覺得,或許有一天,這一切都會有用。就這樣,不知不覺我都已經無罪定讞八年了,忽然顧玉玲找我。我想,那應該就是這個了。立刻答應。如果能幫助我們同理冤案中的人,我的經驗在此雙手奉上。
故宮南部分院案
2006年,在我離開故宮三年之後,我被以辦理故宮南部分院工程總顧問案圖利他人的罪嫌,和前院長、前副院長、兩位建築顧問一起被起訴。我們的案子在一審宣判無罪,二審無罪定讞,全案歷時三年。
那三年真的很辛苦,最辛苦的是調查階段。因為資料不公開。我已經離開故宮三年,手邊什麼資料也沒有,很難回答那些氣勢洶洶,且預設我有罪的問題。待真正被起訴,我當初經手過的公文檔案卷宗公開後,狀況才比較好轉。對我而言規則變得公平,有資料我就可以說明,也可以讓客觀的事實被看見。
和恐懼相處的日子
然而,即使我理性上知道自己沒有犯罪,在官司真正宣判之前,我還是經常一個人陷入恐慌的情緒之中。那是對「溝通」信賴感很低的三年。始終有一個揮之不去的恐懼是:雖然我知道真相是什麼,萬一法院在乎的根本不是真相,而停留在捕風捉影的推測;萬一沒有人在乎真相,就是要入我們於罪,我該怎麼辦?
和恐懼相處的日子,有時好點,有時很糟。我想許多人應該都有這樣的經驗:精神好的時候,不會想太多;精神不好的時候,心裡的陰暗面積會倍數擴大,會無法控制地往壞處想,有一個壞的無底洞就在腳邊而自己正不斷地掉下去。更具體地說,當時我經常感到自己像是住在一個洞穴裡。在洞裡的我,有照明,照得清楚事物。但當我要走到洞外,往外說話的時候,卻不知道外面的人有沒有在聽。洞穴很深,石壁很厚,我的聲音好像被封住了,傳不出去。
現在我已經知道,那時就是比一口長氣。唯一的辦法,是自己去把事實過程、證據建構起來,一次又一次說明,一次又一次整理,直到能夠從洞穴走出去。要自己去把洞穴內外的邏輯理路給接回來,不能被岩壁擋住,不能被懷疑的眼神止語。要一直走,一直走,一直到走到洞外去。我在一審即遇上了認真的受命法官,判決書非常詳細地重建了事實。在我的案子裡,這個過程花了三年時間。

法官從來不看他
但是冤案21年,被判過7次死刑,經歷過70位法官;同為《審判王信福》的演員,徐自強則說,他所遇到的狀況,法官從來不看他,都是在翻卷宗,也不知道有沒有在聽。鄭性澤的經驗也是一樣。當我演審判長,一開始我演得很嚴肅,盯著律師和被告看。他們兩個人都立刻發現問題。導演剛喊卡,阿澤就說,法官不會看被告。聽了他們說,我才意識到,有些案子之所以是冤案—如徐自強案和鄭性澤案,纏訟那麼多年才終於平反,果然還是有原因的。他們遭遇到被忽視、聲音傳不出去的情況,遠比我嚴重。而且他們面對的是死刑。
我們的法官和檢察官都很忙碌辛苦,工作量很大。但受了冤枉、不被聆聽的被告,就像是一個人被留在黑暗的洞穴中,隨時有可能不明不白地付出生命。當初我感到自己被冤枉,所經歷的恐懼不安,是真實的。現在仍然在冤案之中,在法院、在某些社會定見裡發不出聲音的人,也是如此。幽閉的恐懼和孤獨感,請大家試著想像一下。
那洞穴就是我們,那岩壁就是我們
當機構和制度犯錯的時候,我們需要拉住繩索,讓當事人不會被孤獨地遺落在洞穴裡。因為那令他們感到聲音發不出去的岩壁,或許就是由我們的法律制度目前仍有的不足之處,與社會隨口的主觀成見和輕信所構成的。那洞穴就是我們,那岩壁就是我們。因此我們也要負起責任,去打開洞口,讓受害人可以有機會走到洞穴外來。
關於王信福案,和《審判王信福》這部片,廢死聯盟已經有許多文章。我從自己親身有過的經驗、當事人感受的角度寫下這些,希望能為王信福案多喚起一些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