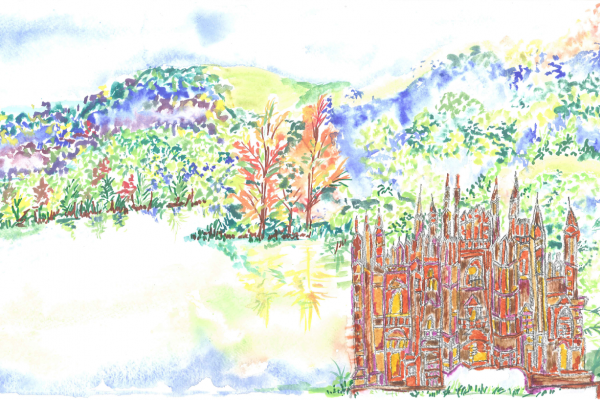電子報
廢死聯盟說的話,是為《廢話》。
在2010年的死刑爭議裡,我們受封為「最邪惡的人權團體」,我們的主張,看起來確實狗吠火車,所以《廢話》也就是「吠話」。知其不可而吠之,汪汪!《廢話電子報》於2012年2月首次發刊,每個月發行的廢話電子報是廢死聯盟實踐與社會溝通的方式之一,我們期許自己用淺白、易懂的文字,透過定期的發刊,持續跟社會對話。
作為一個社會共同體,我們每個人到底做了什麼?
文/李佩雯(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副教授)

馬來西亞籍以台灣為家的學弟,那天突然傳訊給我。
「我真的覺得他應該被判死刑。」
學弟之所以私訊我,主要是因為他知道我支持廢死。
他在得知長榮女大生命案之後,極度氣憤,甚至哭泣。學弟自澄某些程度上反對死刑,「因為有些案子無法排除冤案的可能」,他說。察覺他傳訊當下的情緒極度波動,我跟他說:「我不想在這時候跟你討論死刑,我只希望你的心靈可以獲得平靜。」明白學弟的家鄉同袍之情深受傷害,當時我只想肯認他的不捨與苦痛,讓他盡情流淚。
.............
隔天上課,我以「懲罰為重?還是預防為先?」之題與大一生展開討論。不意外,大一生並不熟悉彭婉如,也沒聽過白曉燕。這兩位女性在我大學時代烙下深刻無比的記憶。那個時準,我和大學女同學們總是買報,討論案情發展,驚恐歹徒逃竄到自家鄰區,感嘆「女人的命怎麼不是命」,我們又會不會是下一條人命。
大一生瞄準了重刑申論,羨慕起鄰國立法鞭刑。
「老師,我覺得死刑太便宜他(加害人)了,一定要慢慢地折磨他。」全班哄堂大笑。
如此沈重的議題,卻惹來全班笑聲連連。馬來西亞學弟如果在場,淚何以堪?
各種形式的懲罰其滿足、彌補的究竟是活著的我們?家屬破碎的心靈?還是為亡者討回正義公道?懲罰也許可以達到某種程度的威嚇,將加害者隔離也能讓活著的我們感到安心。但是長遠來說,我認為不加速將社會網絡補上,牢房以外的世界只會越破越大洞,漏接越來越多人,屆時權力位置小的人(例如女性、例如兒童)的命可能都不是命。
懲罰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是我更希望學生和我一起想想「預防」途徑。
打個比方,曾經在路中央被石頭絆倒的你我,可以選擇一腳把石頭踢走(隔離),氣呼呼地走開,也可以回過頭來思考為什麼那顆石頭會出現在那裡。前者可以暫時免除下一個被絆倒的人,後者卻能長久防止有人在那條路上被其他一再因故出現的石頭絆倒。
因此,長榮女大生一案我們可以停在「將犯案者除掉就沒事了」的階段,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思考究竟「這齣悲劇是如何發生的」:這名男子到底怎麼會長成加害者,受害者又怎麼被迫走上亡命之路。循各線思索,此案每一個相扣的環節都漏接了,以至於不見預防發生。此處我指的預防,不是檢討被害人一類的馬後砲說詞:什麼「缺乏自我保護意識、不懂得結伴同行」。我所謂的預防其實正是自掃門前雪的反義,就在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當中:校方是否重視學校周圍的路線安不安全?里長明知該段路燈經常被偷電,卻無計可施?派出所警方一個月前甫接獲另一名女大生的類似報案,卻未進一步蒐證或加強巡邏?加害者曾經一再偷竊女性內褲的微罪難道不需要任何司法社工與心理輔導的提前介入?所有的日常漏接、推諉和你的皮球不是我的皮球看似無關連,但通通串起來的結果卻是一去不復返的悲劇。
案發後,台南的另一位女大生忍不住向台南女市議員陳情。據報導,她曾因恐怖情人的死亡與性侵要脅,而向校園教官與同一個派出所員警求助。很遺憾地卻換來「會不會太大驚小怪」、「什麼事都還沒發生啊」的粗糙回應。筆者年輕時受某大外語中心外籍教師騷擾時,也曾收到派出所員警此類缺乏性別意識的反應:「妳確定妳跟老師沒有交往嗎?」氣得當時陪著我去報案的男友幾乎對警員掄起拳頭。
說到底,我認為校方、教官、警方、社區管理者、司法單位等皆嚴重缺乏性別意識。上述的人身安全警訊出現時,擁有性別權力的一方並未響起警鈴, 而身處性別權力另一方的女性只好憑運氣每天提著心吊著膽地走過每一條暗路,不確定哪一天會成為不歸路。
祭出嚴刑峻罰的同時,我們應當先問問自己:當社會網絡還來得及補救的時刻,我們是否作為一個社會共同體,各.盡.其.責,一層一層地預先做好防範?走在暗巷裡無需心驚膽顫的社會權力一方,願不願意換位並設法消除女性心中的「彭婉如」陰影?
親愛的學弟,死刑真的不是重點。重點是在死刑之前,當我們在日常察覺任何異樣時,我們每個人到底做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