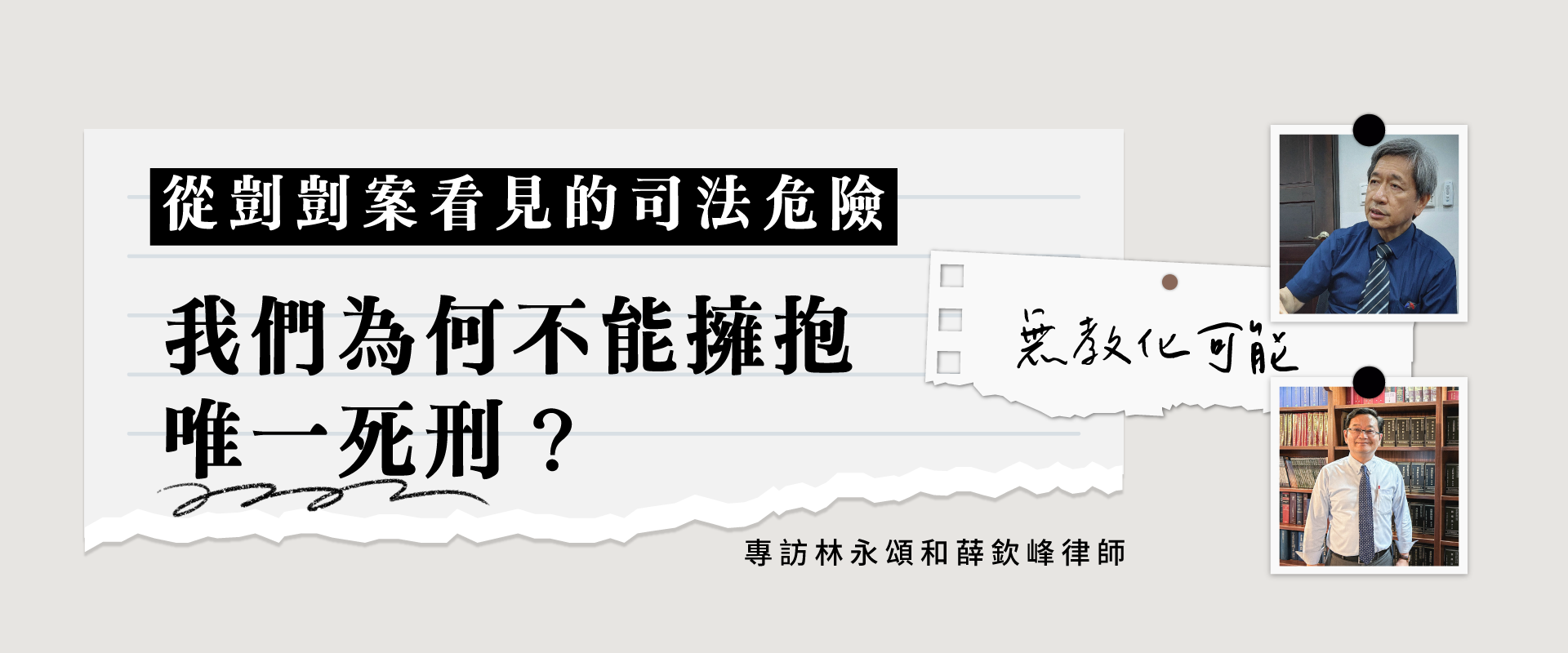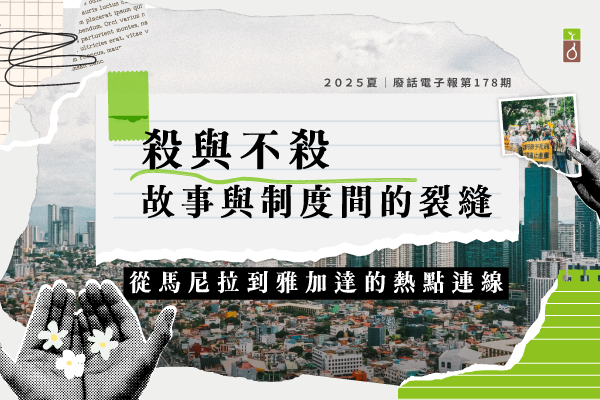電子報
廢死聯盟說的話,是為《廢話》。
在2010年的死刑爭議裡,我們受封為「最邪惡的人權團體」,我們的主張,看起來確實狗吠火車,所以《廢話》也就是「吠話」。知其不可而吠之,汪汪!《廢話電子報》於2012年2月首次發刊,每個月發行的廢話電子報是廢死聯盟實踐與社會溝通的方式之一,我們期許自己用淺白、易懂的文字,透過定期的發刊,持續跟社會對話。
從剴剴案看見的司法危險:我們為何不能擁抱唯一死刑?
文/謝俊彥(廢話電子報特約記者)
「唯一死刑」對你來說是什麼呢?是徹底抹除罪惡的萬靈丹,還是義憤情緒的出口?是嚇阻壞人不再恣意妄為的亂世重典,還是讓無辜者付出不成比例代價的惡法?
今年五月備受關注的「台北保母虐童致死案」(下稱剴剴案)一審結果出爐後,許多關心虐童事件的民眾而言,保母姊妹劉彩萱、劉若琳分別遭判無期徒刑及有期徒刑18年,顯然還「不夠重」。許多網友因此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要求加重虐童者刑責,最重可以判死刑;亦有義憤的群眾上街抗議,在法院外高舉「虐童致死,唯一死刑」的標語。對此,法務部、許多法界人士和政治人物紛紛表示不同意見,指出唯一死刑並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可能使情況雪上加霜。
毫無反抗能力的嬰幼兒受到長時間的凌虐,這種事任誰都會感到憤怒,想要將兇手除之而後快,這種樸素的正義並非難以理解,但為什麼那麼多人站出來呼籲「唯一死刑」是錯誤的呢?
對此,我們訪問了林永頌和薛欽峰兩位在台灣人權及司法改革運動多有耕耘的律師,請他們透過學理、實務上的視角,和我們分享台灣那段曾經歷唯一死刑的時代是什麼樣的狀況?該制度為什麼不可行?它又會帶來哪些不可逆的惡果?
什麼是唯一死刑?
唯一死刑又被稱作「絕對死刑」或「強制死刑」,它指的是對於某些特定犯罪類型,法官「只能」判處死刑,而沒有其他刑度可以選擇。也就是說,當行為人犯下某罪,不論情節輕重或是否其情可憫,唯一的刑罰就是死刑,法官沒有其他的裁量空間。
1995年房仲黃春樹遭人綁架勒贖後殺害,被告之一的徐自強雖然主動投案,並提出不在場證據說明自己並未涉案,但在當時擄人勒贖而故意殺害被害人屬於唯一死刑之罪(2002年修正以前的刑法348條第一項),徐自強自此一路被判處死刑。曾任徐自強案辯護律師的林永頌律師憶該案,表示徐自強被以「擄人勒贖而殺人」起訴,在當時的法律規定下,就算只參與擄人勒贖的過程而沒有殺人,也會被判死刑,更何況徐自強根本是遭到冤枉的。

此外,本案歷審法官都以被害人屍體遭「濃硫酸」燒毀作為關鍵證據,試圖用以證明徐自強有採購濃硫酸及共謀殺人的意圖,因此適用當時刑法第348條第一項規定,應判死刑。因為法官存在強烈「不得翻案」心態,即使後來證據轉向(屍體並非遭濃硫酸燒毀)也堅持維持死刑判決,雖檢察總長三度為徐自強提起非常上訴也都被駁回。
徐案顯現唯一死刑存在許多問題。最主要的是,這種規定讓法官缺乏裁量空間:徐自強明明沒有參與殺人,也缺乏明確證據證明其有殺人犯意,但法官卻必須出於維持唯一死刑的適用,而將徐自強和殺人共犯相連結,甚至採用錯誤的證據進行判決。最關鍵的是,唯一死刑違反量刑正義的原則,不論情節輕重,行為人一率會被判死,所以儘管徐自強沒有殺人,也會被判處和殺人者一樣的刑罰。
唯一死刑剝奪法官量刑空間,且有傷及無辜的危險。
唯一死刑的時代脈絡
「唯一死刑是威權時代的產物,這種制度剝奪了法律對於正當程序的要求。」——薛欽峰(律師;曾任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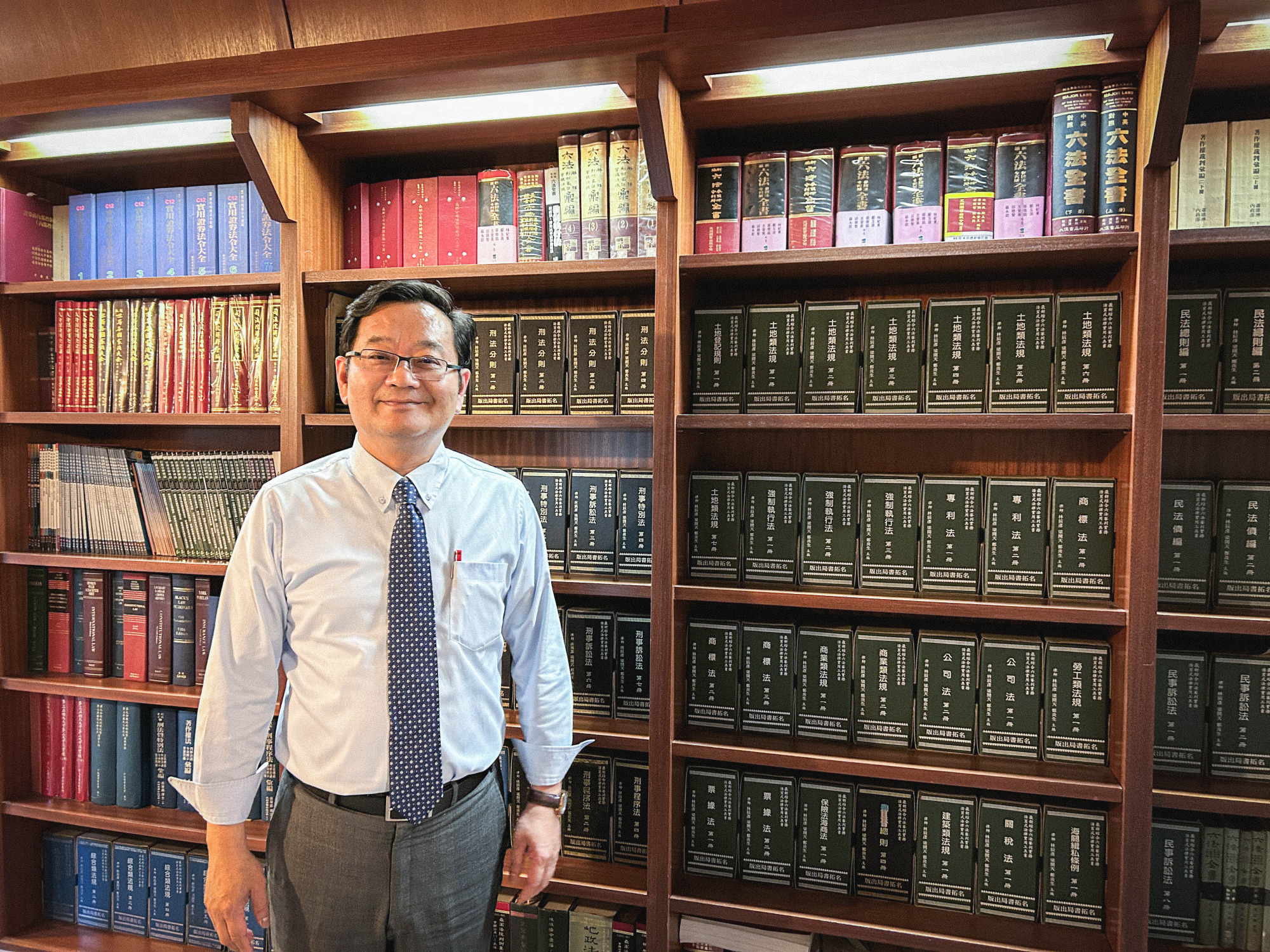
威權統治者最關心的是政權能否安穩存續,為了實現這個目的,當務之急便是盡可能抹除所有會造成「不穩定」的潛在因素,包括重大刑事犯罪(擄人勒贖殺人)、持有危險物品和人民的不良習慣(肅清煙毒條例),當然,也包括「妖言惑眾」的異議份子。
如果能搭上時光機回到76年前的6月21日,我們將會從那一天開始,經歷長達42年的噤聲。那是《懲治叛亂條例》公告施行的日子,那天過後,就算你是平民,若觸犯法律,也會被送進軍事法庭審判。《懲治叛亂條例》最令人聞之色變的便是所謂的「二條一」,第二條第一項:「凡觸刑法100條至104條罪者,處唯一死刑。」
那是用死刑來對付異議人士的年代,只要法官認定你有顛覆國家的「意圖」,就會被判刑;任何不見容於當局的行為都可能被冠以「意圖破壞國體或竊據國土而著手實行」的罪名;讀了不合於主流政治敘事的書籍、接觸政府不希望你見到的人,都可能成為「思想犯」、「政治犯」而遭「二條一」起訴、定下死罪。
薛律師表示,在實際接觸許多案子、理解時代及多數國廢除死刑的背景之後,就可以理解從文明及人權保障反威權的脈絡,到對死刑制度的論述與立場。唯一死刑是威權的工具,壓抑獨立審判的法治發展。
唯一死刑的問題
薛律師回憶起他剛當律師時,便注意到當時每年都要處決6、70位死刑犯。威權體制下,唯一死刑加上速審速決,許多重大案件都到二審就結束、定讞,也因此判處、執行很多死刑。
大眾覺得面對犯罪速審速決、重判死刑最好,但是這樣的司法制度讓當事人失去上訴的機會,將使許多被告失去救濟空間,且嚴重違反比例原則。看似高效率,實則是以錯殺的無辜人命獻祭而來,草草結束的除了案子之外,被告的性命和真相也將隨之被輕率地抹除。這樣的制度容易造成司法不公,對社會而言帶來的傷害很大。
廢除唯一死刑是趨勢
如果還有唯一死刑,能夠遏止犯罪、懲罰加害者嗎?薛律師認為,這樣的狀況下,加害者更會躲起來拒絕投案,因為無論如何結局都是死路一條,對於被害人也會產生更致命的結果。早期擄人勒贖唯一死刑,那麼人質就更被容易殺害,減少加害人被抓的風險;如果現在酒駕、虐童唯一死刑,難保原本非故意造成的犯罪,可能會演變成加害者認為「乾脆把被害人弄死,一不做二不休,減少一個目擊者也許還能逃過被逮捕。」
現在世界各國即使還保有死刑,也已經逐步放棄唯一死刑(例如馬來西亞)。仍保有唯一死刑的國家並不多,而且集中在威權專制的國家當中。合理的刑罰應隨犯罪情節輕重有所差異,行為人才有機會衡量行為與成本之間的關係,此外,社會大眾才有機會了解犯案動機,有助於未來防範再犯。
剴剴案引起許多人對於司法制度的思考,也看到為數不少的民眾表現出對司法的不信任。人們在面對這類重大刑事案件時,習慣把樸素的正義化作想將兇手除之而後快的怒吼。
但矛盾的是,當你不信任司法,認為司法可能錯殺不該殺的人、放過該殺的人時,你為何又將奪取人命的權力,大大方方地交給司法制度呢?怎麼還會相信這個你不信任的司法制度,有公平決斷生死的能力呢?
司法上誤判的可能性,就是我們應該對死刑有所警惕的主要理由。
此外,儘管多數人在直觀上可能認為死刑或嚴刑峻法是「治亂世」的神丹妙藥,但台灣走過槍擊案頻傳、台灣治安最糟的時期,林永頌律師和薛欽峰律師一致認為,死刑的存在與治安,兩者並不存在因果關係。換句話說,如果死刑真的能有效防止犯罪,那麼死刑執行數量最多的時期,台灣的治安就不會那麼糟。
回到剴剴案,這是台灣社會全體的重大傷痛,雖然說案件發生後才開始關注兒童權益與社工、保母制度、收出養制度的結構性問題,都已經太晚,但我們仍要亡羊補牢,著手行動。唯有如此,才有機會擋下下一場悲劇。在付諸行動的同時,也切莫重蹈覆轍。憲判八已經明文「唯一死刑違憲」,不要讓唯一死刑這種危險、輕率且缺乏程序正義的制度,再度伴隨案發當下所生的激情和憤慨,一起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