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報
廢死聯盟說的話,是為《廢話》。
在2010年的死刑爭議裡,我們受封為「最邪惡的人權團體」,我們的主張,看起來確實狗吠火車,所以《廢話》也就是「吠話」。知其不可而吠之,汪汪!《廢話電子報》於2012年2月首次發刊,每個月發行的廢話電子報是廢死聯盟實踐與社會溝通的方式之一,我們期許自己用淺白、易懂的文字,透過定期的發刊,持續跟社會對話。
將倡議帶上大銀幕——人權與藝文工作者的協作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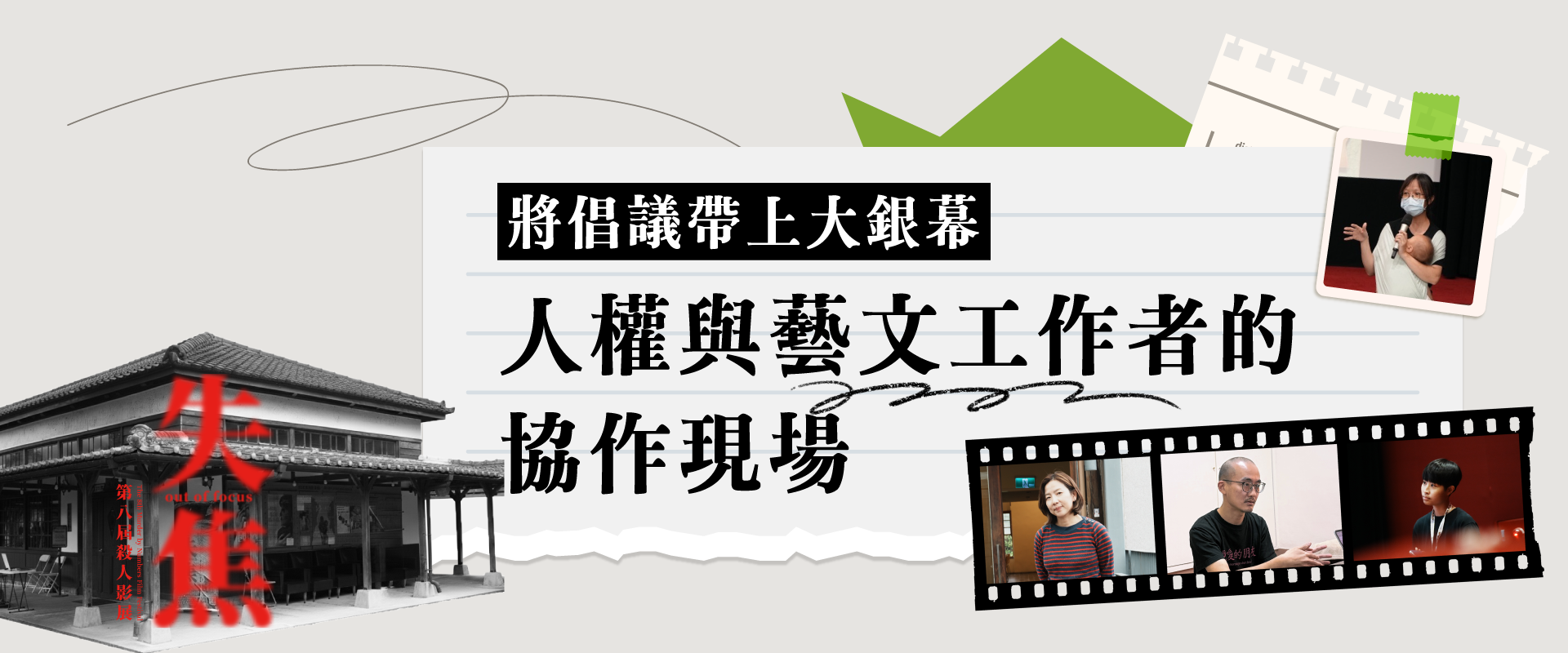
文/李玗靜(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倡議專員)
三年一度的殺人影展從2004年開始舉辦至今,已經來到第八屆。議題型NGO跨域做影展,需要許多夥伴的協力,才能堅持跨越21個年頭。而在影展中,我們總被精緻的作品、出席影人,或是映後座談的與談者吸引目光,鮮少關注到其中的幕後推手。因此本文特別訪問到這次影展的兩位場地協力,光點華山電影館的行銷公關經理蘇菲、花蓮鐵道電影院的場地負責人雅婷;以及第八屆殺人影展統籌,影展工作者小佑、廢死聯盟倡議主任禮涵。
蘇菲:與殺人影展同行十二年
蘇菲自光點華山電影館於2012年開館後便在此工作至今,而殺人影展台北場也在隔年落腳於此,由她承接場地相關事務。從第四屆到第八屆,我們已與蘇菲合作五次,長時間的合作也培養出相當良好的默契。
在進入電影產業之前,蘇菲原先從事出版工作。後來因為出版業環境相對艱困,加上自己本就喜愛看電影,於是轉而來到新的電影場館工作。她回憶起光點華山剛開館時的情景,大家幾乎都是新人,只能一邊做、一邊學。
「對殺人影展的第一印象是什麼?」這是我在列訪綱時最先想到的問題。畢竟,對許多藝文工作者而言,聽到「廢死聯盟」這個名字,或許會下意識地退避三舍;而殺人影展卻能與場館維持穩定而密切的合作,這讓我格外好奇其中的原因。蘇菲回應:「我自己本身就支持廢死,也覺得廢死是個很艱困的NGO。大家總是帶著情緒來討論這個議題,所以我當時會想,也許用影展這樣的形式,比較不會讓大眾產生抗拒。」
她也提到,殺人影展第一次在光點華山舉辦時,便讓她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僅整體規劃有組織性,索票率與滿座率也都相當高。隨著屆數推進,蘇菲觀察到影展從最初的較小規模,逐漸拉長天數、增加片量,協力單位也一年比一年多。「感覺資源慢慢都進來了!」她說,後來甚至會主動向其他單位分享,建議可以參考殺人影展的經驗。
我們也趁機向蘇菲請益,從她的角度來看,影展是否真能為議題倡議帶來效益?她的回答十分直率:「影展一定是有效的,近年才會有這麼多單位都想辦,不然辦講座就好啊!」聽到這句話,我不禁想,殺人影展應該還能再走下一個二十年吧。
訪談最後,蘇菲不忘補充她對影展名稱的觀察:「我覺得『殺人影展』這個名字取得非常精妙,轉個彎、卻又聳動,可以打到很多『不排斥廢死』的人。」
 採訪當天,蘇菲帶著愛犬宅宅一同受訪。(圖/張馥如拍攝,廢死聯盟提供。)
採訪當天,蘇菲帶著愛犬宅宅一同受訪。(圖/張馥如拍攝,廢死聯盟提供。)
雅婷:用場館改變觀眾
殺人影展在本屆首次巡迴至花蓮,因為花蓮狹長的地理以及人口結構因素,鐵道電影院的場地負責人雅婷在活動結束後特地寫信鼓勵我們,不要因為觀影人數不及台北而感到灰心。對於我們來說無疑是非常暖心的舉動,因此此次在挑選影展回顧系列的受訪者時,我們第一個就想到了雅婷。
談到第一次接到殺人影展的合作邀約,雅婷坦言當時「有嚇到」,也是第一次知道有這樣一個影展的存在。「第一印象是覺得『很直接』,因為名字就叫『殺人影展』。」雅婷認為這樣的命名既直白又強烈,能夠成功引發好奇。
「看到片單後我覺得很特別,因為有些片子本來就是我自己有關注的作品,例如《帶針的女孩》之前就在我們這裡上映過。」她提到,從片單中其實就能隱約看出影展希望引導的討論方向,每一部作品背後都不只是故事本身,而是指向更大的社會議題。
讓雅婷印象最深刻的,是殺人影展對於映後座談的重視。「每一場都有與談人,而且大多是當地的學者、專家,這點跟很多影展很不一樣。」她觀察到,不少影展在北部或西部已經運作多年,但來到花蓮時,未必每次都會邀請與花蓮有連結的人選來參與對談;有些場次甚至只有放映影片,沒有任何映後交流,或是僅由影人進行分享。相比之下,殺人影展刻意尋找在地與談者,讓討論更貼近地方脈絡。
「花蓮的觀影群眾、生活習慣和節奏,其實都跟西部、北部很不一樣。」雅婷指出,正因如此,能夠真正與在地連結、邀請熟悉地方情境的人來對談,對她而言是一件非常重要、也非常難得的事。「這也是我覺得這個影展很棒的地方。」雅婷說。
進一步談到花蓮與台北的差異時,雅婷指出,台北的觀眾往往能夠主動挑選自己想看的電影;但在花蓮,因為場館數量有限,更多時候是「場館選什麼,觀眾就看什麼。」久而久之,場館其實會反過來形塑觀眾本身。她分享,鐵道電影院長期經營下來,已經培養出一群穩定的觀影族群,也因此在這次影展期間,收到常客回饋表示:「透過這些影片,發現事情跟自己原本想的很不一樣。」
雅婷也認為,以影展的形式推廣議題相當不錯,若能每年持續在同一個場域、同一個時間點舉辦,累積下來一定會看見成效。「因為在觀眾的體感上,會慢慢形成一種『到了這個時候,就要關心這個議題』的身體記憶。」
這次與鐵道電影院的合作,讓我們期待未來能再次帶著殺人影展回到花蓮。

小佑:從顧問到影展統籌的身分轉換
小佑長期從事影展相關工作,約莫在殺人影展第六、七屆之間,便已在部分放映活動中從旁協助殺人影展,但當時較偏向顧問角色。今年則首次與禮涵搭檔,正式共同擔任本屆殺人影展的統籌,全面投入影展的規劃與執行。
談起一開始接觸議題性影展的感受,小佑坦言,最初其實有不少擔心。「議題影展的立場通常都很明確,一開始最害怕的就是社群上的攻擊。」他回憶,曾經擔心活動是否會引發衝突,甚至思考過現場是否需要額外準備安全措施,覺得這並不是一個「容易辦」的影展。
過去小佑多半負責的是執行層面的工作,較少參與選片環節。但他也觀察到議題影展的選片標準,往往不是視覺或聲光效果,而是策劃者在那個時刻,想要與觀眾對話、分享什麼樣的內容。「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會看到很多不同工作者的努力,也看得到他們受挫的痕跡。」
小佑也提及,自己感受到議題影展的另一個困境:影展實際觸及的觀眾,與原本設定的倡議對象,有時並不完全重疊。理想上希望被討論、被看見的群體,有時候卻是最難走進影廳,或者相對缺乏餘裕參與藝文活動的人。在這樣的結構性落差下,「透過影展完成倡議」本身就存在限制。然而整體而言,小佑仍肯定影展對議題倡議的幫助。他認為,影展至少能觸及一群非常愛看電影的觀眾,用相對「軟」的方式把議題帶進影廳,再透過映後座談,讓這些人與議題產生更深的連結與交流。
回顧最初從旁觀察殺人影展時,小佑提到,自己曾被社群中常見的一類留言問倒——「如果是你的至親被殺害,你還會支持廢死嗎?」他分享,後來在與一位朋友的對話中,對方引導他思考:「如果我不同意殺人是合理的行為,那為什麼可以授權給國家殺人?本質上其實是一樣的,都是殺人。」那一刻,他形容自己像是被「點醒」了。「在跟廢死聯盟合作之前,我其實沒有特別深入思考過死刑這個議題,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收穫。」
談到籌備過程中最困難的部分,小佑提及,議題影展的規模通常不大,反而讓人必須身兼多職。相較於大型影展分工細緻、只需負責其中一小塊工作,這次他必須同時理解每一項工作的細節與時程,「這其實不是我擅長的事,我比較需要被別人追進度。」他笑說自己一度覺得相當崩潰。
而那些過去只在耳聞中存在的「棘手狀況」,也在這次一一化為實務經驗:跨國片商聯繫的困難、各影廳放映規格的變動、《親切的金子》需另行處理投影字幕的安排,甚至是原本預計出席的影人 Sunny,在節目聯繫過程中意外離世。面對這些突發狀況,他必須一邊關心夥伴的情緒,一邊保持理性,持續推進工作進度。小佑說,正是這些過程,讓他在專業與心理上,都有了明顯的成長。

禮涵:讓電影成為不說教的倡議方式
本次殺人影展的統籌角色,由廢死聯盟倡議主任禮涵擔任,一肩扛起對內與對外的溝通協調。她形容自己對殺人影展的想像,是一個「平易近人、可近性很高」的場域——不需要很高的成本、不需要先備知識,讓更多人能自在地走進來,「這是我們一直想要塑造的氛圍。」
已在廢死聯盟從事倡議工作六年的禮涵,今年是第一次以影展統籌的角色投入,實際負責的內容與以往大不相同。找片商、溝通合作、處理前端事務,都是她過去較少接觸的工作。這次能與長期從事影展工作的夥伴小佑合作,讓她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一個專業影展工作者如何處理前端流程,對自己而言是難得的學習。
談及籌備過程中的困難,禮涵認為「抓時間進度」是整個計畫裡最難的一件事。影展籌備的時間跨度很長,且每一個節點都環環相扣,「前面一個地方延遲,後面就會全部被拖著走。」她笑說,過去的工作習慣讓自己保有較大的彈性,但在影展統籌的角色中,這樣的彈性反而變得困難,也更真切地感受到時間管理的壓力。
在繁重的行政與協調工作之中,禮涵最感到開心的時刻,是能夠把自己欣賞的人帶進來一起工作。「用自己的專案,把欣賞的價值帶進來,甚至可以藉由這個合作,把欣賞的人推廣出去,這件事本身就很開心。」她形容,那是一種把理念化為實際行動的過程。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禮涵也經歷了一段拉扯與掙扎。她提出一個反覆思考、卻始終沒有答案的問題:殺人影展這個品牌,究竟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與「廢死聯盟」的名字掛鉤?她指出,許多人一聽到「廢死」便會下意識卻步,若因此錯失走進影展、接觸議題的機會,總讓人感到可惜。也正因如此,有時會希望殺人影展能以相對獨立的品牌運作,讓更多人願意先踏進場域。
但也忍不住擔心,若大家始終不知道這是由廢死聯盟所舉辦,似乎也同樣可惜。於是,在宣傳策略上,是否要不斷強調「這是廢死聯盟主辦的影展」,便成了一個不斷回到眼前、卻難以取捨的問題。禮涵坦言,這樣的拉扯至今仍未找到一個確定的解法。
即便如此,禮涵對影展作為倡議媒介,仍抱持高度肯定。「一定有一群原本沒有關注議題的人,是因為電影而走進來的,而且我的經驗告訴我,這不是少數。」她也觀察到,許多組織與團體近年也開始舉辦影展,本身就反映出這群觀眾的存在與重要性。「電影不說教、不侵略,而是透過故事與畫面,讓人自己去意會。這樣反而更容易留下來,因為與自己的生命經驗產生連結。」

回顧整個籌備過程,讓禮涵印象最深刻的,還有在這個位置上所建立的人際連結。她說,能夠認識許多不同領域的人,並在合作後逐一表達感謝,是她非常珍惜的部分。「我會很清楚知道,是誰、用什麼方式實際幫助了我,這份善意變得很具體。」這些具體而真實的支持,也讓她更加確信,這些善意值得被記得,也值得被好好回應。



